9岁开始学日语的竺家荣,直到四十岁才等来独自翻译一本书的机会,然而面对的却是一本“有伤风化”的小说。

“译者”似乎一直是一个相对低调的职业,他们所做的努力之一或许是尽量使自己趋近于透明,把一个更真实的原作者呈现出来。但我们这次想要把他们从原作者的背后带到台前,他们是一部作品的合作创造者,有辛劳,有才华,有热情,也有故事。
人们所熟知的译者大都是老一辈的翻译家:傅雷、杨绛、草婴、朱生豪、钱春绮、柳鸣九……他们最早把一批世界经典作品带入了中国。相比起来,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可能也越加忽视了译者的地位。每每听到和译者有关的消息,大多与负面内容有关。这也将一些问题摆在了眼前:何为优秀的翻译?翻译自由度的底线何在?翻译又如何应对网络和流行文化?
我们选择了一些当代的优秀译者,他们大都正值壮年,耕耘在不同语言的土壤中,已经饶有成就,并且依然处于旺盛的产出期。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等等方面均有涉及。每一篇包括译者的翻译故事、探讨翻译相关问题的同题问答,以及译者本人推荐的自己的代表译作。
我们称之为“新译者访谈”系列,这里的“新”对应的是读者们更为熟悉的老一代译者。这应该是第一次,让这些译者们以群像的方式将自己的故事讲述出来。
今天,我们推送的是“新译者系列”访谈的第九篇,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日语译者竺家荣的故事。
那天的场景竺家荣至今依然历历在目。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珠海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突然登门,手里拿着一本日文小说。竺家荣当时只翻译过一个短篇,但编辑只通过这个短篇,就认定竺家荣是翻译这本书的不二人选,请她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翻译出来。接过这本名为《失乐园》的小说后,竺家荣随便翻了几页,大段大段露骨的性爱描写跳入眼中。
“不行不行。”她把书递回去,拒绝得很干脆。编辑没却有放弃,二次登门,再三说:“我跟你说两点你一定会改主意。第一,允许删节以及朦胧化处理;第二,翻译了这本书,你就出名了。”从九岁开始学日语的竺家荣,直到四十岁才终于等来了独自翻译一本书的机会,然而面对的却是这样一本“有伤风化”的小说。翻还是不翻?竺家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竺家荣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解放前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工学系,曾在鞍钢任电力自动化工程师,后来因工作调动举家迁到北京。竺家荣在鞍山出生,在北京长大。父亲虽然主攻理科,但文史兼通,会英语、俄语、日语等几门外语,家里藏书丰富。家里姐弟三人,唯有竺家荣沉迷于这些藏书,“姐姐弟弟都比较外向,在家里待不住,只有我个性好静,不大喜欢出去玩,常常在家里看书,所以从小就对书有一种偏爱。”希腊神话里的九头蛇以及自恋的美少年被自己的化身拖下水的画面、百科图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里的爱情故事、以及各种小人书等等,构成了竺家荣最初的文学记忆。
1964年,为应对外交人才短缺的问题,周恩来指示“外语要从小学起”,国家开始实行一项从适龄儿童中选拔外语人才的培养计划。全国开办了8所外国语学校,招收从9岁开始学习外语的小学生,其中有两所在北京。“外语学校主要由外国教师教课,直升外国语大学,将来培养出来都是大使或大使夫人!”小学二年级的竺家荣坐在教室里听着老师介绍情况,非常向往。不过竺家荣虽然成绩还可以,但外貌并不突出,老师只推荐了班上最漂亮的“四朵班花”,没有推荐她。
竺家荣懊丧地回到家,跟母亲讲了这件事,得到了母亲的支持:“你想去的话,就去跟老师说说呗”。第二天,竺家荣在班上同学的鼓励下壮着胆子跟老师说“我也想去参加考试”,老师看了看她,说了句,“那就给你加一张表吧”,就这样竺家荣报上了名。
接下来是笔试、面试、身体检查,过了一关才能进入下一关,在忐忑的等待中,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不久后的一天,竺家荣在家里听到有人“蹬蹬蹬”地跑上楼来,她开门一看,是老师,吓了一跳。这位四十多岁的女老师跑上四楼,气喘吁吁地一把抱住了竺家荣,叫道:“没想到,你真棒!”后来竺家荣得知,外语学校考试竞争相当激烈,而她是班上唯一一个通过了考试的学生。

竺家荣很想学习德语、法语这些听起来很洋气的语言,结果被分到了日语专业,原因竟然是她的视力问题。竺家荣的眼睛先天屈光不正,她从小看书便要戴上奶奶的老花镜,但依然十分费力,看一会儿就得闭眼睛休息一下。外语学校要求的视力是1.5,竺家荣只有1.0。她记得检查视力的是个高大的很帅的叔叔,对她说:“小妹妹别紧张,给你写1.2吧。”虽然过了体检这关,但因为视力不达标,竺家荣被分到了没有人愿意学的日语专业。那时中日两国尚未建交,学日语很受歧视,在寄宿制的外语学校里,学日语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但父亲的话给了她很大信心:“好好学,中国和日本用不了多久一定会建交的。”七年后的1972年,这句话果真变成了现实。
但还没等到中日建交,中国国内局势开始动荡。竺家荣刚进入外语学校两年,文革爆发了。学生们纷纷变成了红卫兵、红小兵,到处充斥着政治口号、大字报、毛主席像章、“忠字舞”……竺家荣对政治始终不太关心,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依然一天到晚只想看日语书,因此被大家批评为“白专”。“我记得到后来,全班都是红卫兵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不是了!”17岁那年,竺家荣从外语学校毕业,只有“根红苗正”的毕业生才能分配到外交部、公安部等国家机关,而成绩全优的竺家荣被分到一所中学,成为了一名日语老师。
从17岁到22岁,竺家荣在丰盛中学度过了五年茫然的青春岁月。文革还在继续,学生们根本不愿意学习,竺家荣比这些十三四岁的学生们大不了几岁,作为小班主任,面对调皮捣蛋、无法无天的学生常常是束手无策,她的自行车经常被坏孩子破坏,只能推着走回家。她还得经常带学生去工厂农村开门办学,也曾下放到五七干校受了半年再教育,养过猪、干过各种农活。“对这段日子我不太愿意回首,感觉自己的青春都被耽误了。当时我们去外语学校时,老师说你们的学校是宝塔尖,你们将来就是国家的栋梁,没想到如今从那个宝塔尖上掉到底层,觉得特别失落,不知道将来的出路在哪里,只能整天混日子。”还不到二十岁,竺家荣就长出了白发。
1977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恢复了高考。竺家荣感到机会终于来了,非常兴奋。“恢复高考就等于拯救了我”。她报考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由于“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竺家荣“落了选”,最后被黑龙江大学录取。“虽然必须离开北京,但只要不再当中学老师,我死活也要上大学。”由于有从小学日语的底子,竺家荣直接跳到了二年级。很快国家又开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1979年竺家荣考入了国际关系学院读研,1981年毕业。在这四年的时间内她迅速地拿下了本科和硕士的学位,然后留校任教,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
对竺家荣说,当初学日语是一次偶然,但走上翻译道路却不是偶然的。留校任教之后,竺家荣几乎把全部时间投入到了教学和家庭中,一直到四十多岁,才翻译了人生的第一部书。这其中15年的时间“好像都荒废掉了”,但竺家荣说,自己心中一直保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做翻译。
从上学的时候起,竺家荣就不是那种特别受老师重视的孩子。“毕竟不是能歌善舞,嘴也不是那么甜”,加上视力天生不好,竺家荣说,自己从根儿上来说是一个自卑的人,到现在都是这样。“我属于自尊心极强的一个人,自尊心极强的人,往往自卑感也很强。我总觉得,自己不善于与人打交道,但是学习还可以。兼通中日两种语言以及爱好文学的底子,因此长项很可能是做文学翻译了,只有在翻译中,能够感受到快乐,只有翻译才能使自己获得尊严。后来的发展也多少验证了自己的这个预感。”
在中学教书的那五年,竺家荣就曾几次向学校提出想要调走,去做与翻译有关的工作。成天与一帮学生混在一起让她焦头烂额,她觉得“搞翻译不用跟人打交道,管我自己就好了,至少是清净”,但学校始终没有同意。大学期间,竺家荣也会自己找些日语文章,纯粹出于兴趣“翻译着玩”。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带着学生们集体翻译过一本《日本民间故事》,竺家荣在其中翻译了一篇童话故事,对翻译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之后竺家荣也翻译一些作品,给杂志投稿,但从来没有得到过回复。
在大学任教了十五年之后,竺家荣受邀去参加在武汉召开的三岛由纪夫研讨会,在研讨会上结识了国内知名日本文学翻译家叶渭渠。叶渭渠当时正在组织人翻译一些日本文学作品,看到竺家荣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后,对她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想不想试着翻译一些作品呢?”竺家荣听了喜出望外,“太好了,我这么多年苦苦寻求,一直找不到门槛……”由此,她获得了人生当中第一个翻译机会——安部公房的短篇小说《狗》。她翻译得极其认真,这篇翻译处女作收录在安部公房作品集里,由珠海出版社出版了。
出乎意料的是,不久珠海出版社的编辑亲自找到了竺家荣的家里,带着一个月前刚刚在日本出版并引起轰动的《失乐园》。“你看看这本书,我们希望尽快翻出来,越快越好。”出版社希望赶在台湾的前头,让它的简体中文版尽快面世。看到里面大段大段的性爱描写,竺家荣把书推了回去。但执着的编辑隔几天再次上门,同意进行删节和“朦胧化”处理,并说,你既然想做翻译,就应该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希望再慎重考虑一下。

经过再三考虑,竺家荣最终没有错过这个机会,“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硬着头皮上阵了”,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整个人都陷入了《失乐园》之中。《失乐园》出版后,立刻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几乎到了尽人皆知的程度。但是那时国内的版权制度极不完善,合同也不正规,出版社甚至拖着不付给竺家荣稿费。不过这本书也确实给竺家荣带来了名气,一时间书店里出现了许多渡边淳一的盗版书,都冠上了“竺家荣”的名字,《失乐园》的盗版更是层出不穷。
《失乐园》在中国出版后,同日本一样,评论也是毁誉参半,不过比起这本书在日本的评价,在中国批评的声音反倒要少一些。竺家荣觉得“我们中国人往往习惯于站在自己的文化角度上去解读,把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殉情理解成自杀谢罪,或者认为渡边淳一这样写是在批判日本社会的堕落,这种解读可以说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 。但是这些“误读”反而助推了《失乐园》的传播,也正是在这些误读下,《失乐园》得以安全过关,并畅销多年。
在竺家荣看来,《失乐园》探讨的主题是与自《源氏物语》以来的“物哀”一脉相承的。“物哀”是对事物的一种感伤,或者说深刻的体验,在男女之情上表现得最为典型。”作者通过小说男女主人公所陷入的婚外情,深刻地探讨了婚姻和爱情的含义。在日本的“好色”美学传统中,爱情是灵与肉的和谐统一,而婚姻往往导致激情逐渐淡薄,爱情也随之消亡。小说中男女双方的殉情,是为了避免重蹈婚姻的覆辙,要在快乐的巅峰、最美的时刻结束生命。当然,作者绝非在推崇殉情,是希望人们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不要失去人生的乐园,竺家荣补充说。她前后翻译了十来本渡边淳一的作品,几乎每本都专门写了译后记,详细探讨渡边文学的美学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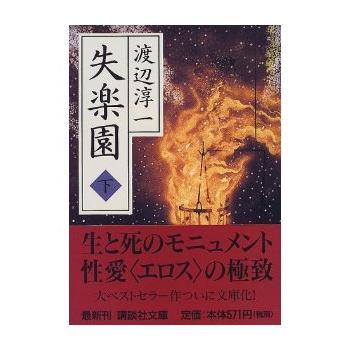
竺家荣说,《失乐园》日本版的封面是耐人寻味的。正面是熊熊燃烧的火焰,封底则是盛开的樱花,这里边含有很深的寓意。火焰象征燃烧般热烈的情欲,将一切化为乌有,而樱花则以其盛开时的美艳,凋落时的决然,,让人联想世事无常,爱的短暂。渡边所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生死观和美学观:死亡是绝对的、无限大的“无”。这种“无”不是西方式的虚无主义,而是东方式的虚无,所谓“无中万般有”,蕴藏着丰富的东方文化的内涵。
当年她曾因《失乐园》有着大量性描写而拒绝过出版社的翻译邀请,如今竺家荣认为,这些不拘一格、不受束缚的日本文学,“能够让中国读者接触到多种文学表现,看到各国文学对人性的多方面探究,拓展视野,善莫大焉。翻译是一个构筑人类精神的巴别塔的神圣事业。”这也是她投身文学翻译的目的之一,也可以说是一种使命感。
翻译《失乐园》之后,竺家荣虽然有了一些名气,但并没有因此大红大紫。她一边继续在学校教书,一边断断续续翻译了十几本书。2002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由于评职称不顺利等原因,竺家荣又一次陷入了低谷,如同在丰盛中学的那5年一样,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表任何译作。“我天性敏感,柔弱,一旦遭遇挫折,很难振作。可以说当时完全看不到出路,对自己对人性对社会都感到绝望,即便是最喜欢的翻译也觉得毫无意义。用现在的说法有点忧郁症的样子”。“总觉得这个社会不公,无论你多么努力,最终人家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地否定掉你” ,因此得出结论,“一切都是虚无,还是什么也不做为好。”竺家荣没有再争什么,她开始自我封闭起来,2005年,以副教授的职称退了休。
就在退休的第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找到竺家荣,带来了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请她翻译。竺家荣翻开书,第一页第一行是这样一句话:“一个雨天,我来到了这个家。”她当即便感到,这是一本好书,而且自己也一定能把它翻译好。出版社的编辑也像多年前《失乐园》的一幕重演一样对她说,只要您翻译,这本书一定会畅销。
竺家荣又一次犹豫了,自己以前翻译的都是些经典作家,从来没有翻译过这种青春文学,而这位作者的年纪几乎跟自己的女儿一般大。但她还是决定挑战一下,“我觉得作为译者应该什么都可以尝试,应该挑战一下自己,就像演员不能只演一个角色,那就模式化了”。《失乐园》的成名让竺家荣在很多人眼里已经定了位,仿佛她就是一位日本情色文学的翻译专家,甚至有编辑拿来一本名叫《性骚扰应对》的书请她来翻译。竺家荣想,自己应该“跳出圈子,翻译一本清纯的作品试一试”。
尽管年龄相差一代人,竺家荣却觉得自己跟青山七惠是有缘的。青山七惠作品当中处事不惊的淡然笔调,很接近日本传统文学中的《枕草子》,让竺家荣颇有些感慨。“我在中国见过青山七惠,跟她一块儿吃过饭。这个年轻人很是老道,真是很成熟,对什么事都很淡定,好像什么都无所谓。她对命运是一种承受的态度,觉得不一定非得改变。”相比起来,竺家荣觉得自己都不够成熟,有些“童心未泯”。“我觉得跟她能学到一些东西,这种处事态度挺好的,很淡然,不能太纠结于一些事情。怨天尤人只能制造负面情绪,无助于自我的提升。”

《一个人的好天气》的畅销程度甚至超出了竺家荣的预想,一度成为了一本在中国年轻读者群中引领潮流的书,尤其是很多80后90后,很喜爱这本薄薄的小书。由这本书而诞生的一个词“飞特”(Freeter)成了年轻人热衷的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固定职业,靠兼职打工来维持生计。这本书也让竺家荣的名字第一次真正为读者所知,很多出版社慕名而来。“从这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到现在为止,竺家荣已经翻译了大约有60多本书,多达二十多位作家,其中包括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安部公房、太宰治、大江健三郎以及当代许多活跃的作家。通过翻译,她也重新找回了自己。“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对我而言,大概是我译故我在吧。翻译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每翻译一本书,都是和一位智者对话。读者的鼓励也总是使自己倍感幸福。最终从翻译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竺家荣一直受到学校的返聘,继续做日语专业的硕士生导师。一周两天,竺家荣到学校教学,剩下的五天,就待在北京郊区的家里做翻译。竺家荣尽可能减少交际应酬以及娱乐等,很少出门,每天从早上八点吃完早饭,一直埋头翻译到晚上十点,每小时翻译几百字,一天下来的翻译量大概是五六千字。不论经典文学还是大众文学,竺家荣不怎么挑剔,她觉得翻译跟个人的喜好无关,译者只是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但她唯一挑剔的是,要给她足够的时间,让她在质量上反复地打磨。
竺家荣说到自己的个性,其中之一是“任性”,“想做什么就非要做什么,认定一件事就去做,而且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考虑后果得失,总是想得很单纯”。她觉得在生活中这种任性也许是一种缺陷,但在翻译中,它会转化成优点,因为她比较“较真”。
过去,丰子恺翻译《源氏物语》,是四年磨一剑,而今大多数出版社为了追求效率,催着译者三四个月就要翻译出一本书来。因为时间问题,竺家荣推掉过好几本书。樋口一叶是竺家荣很喜欢的作家,但她的作品距今年代久远,文白夹杂,又引用大量典故、民俗等,翻译难度很大。虽有过几次机会,竺家荣都要求出版社给她一年的时间来翻译,但出版社等不了那么久,她只好遗憾地放弃了合作。

竺家荣说,在翻译中,最花费时间的不是翻译初稿,而是修改的过程。每一份译稿,在竺家荣手里都要经过五六遍以上的打磨。第一遍是整体的翻译,第二遍是逐字逐句地再将译文跟原文对照,看看有没有漏译和错译,这期间要大量地查字典,把每一个词语的含义搞明白,准确翻译过来,最花费时间。诸如各种蛋糕、点心或是日式料理、西餐的不同做法;棒球和排球、围棋等的游戏规则;各种典故俚语方言外来语;外国人名地名书名植物动物名等等,这些都要仔细查阅资料。有时几个词就要查半天的资料;第三遍是润色和修饰;第四遍是通读一遍,看看哪个句子别扭,把它改得“顺一点”;第五遍是检查标点符号等细节;第六遍是把稿子暂时放下,隔几天再拿起来看看是否还有什么问题。最后才是定稿。
润色是翻译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竺家荣所追求的目标是尽量做到深入浅出,少有生僻词语,句子符合中国语的习惯,让读者阅读起来能够像行云流水一样顺畅,不会磕磕绊绊。她用了一个比喻,翻译就像做菜,原作就像原料,都是上等的东西,就看译者怎么把菜做出味道,让人产生吃下去的欲望,在水平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润色和打磨就变得举足轻重了。比如渡边淳一的语言尽管细腻精致,但日语词汇远不如汉语词汇丰富,同样一个词语在原文中会反复出现,难免会显得单调乏味。竺家荣尽量做到一个词语不重复出现多次,变换不同的中文词语,比如 “妩媚、柔媚、娇媚、千娇百媚、娇艳、娇嗔、娇滴滴”……
平时竺家荣有一个笔记本,遇到新鲜的词语就会记下来,以备翻译之用。“可见,中文的功底太重要了。常听学生说,虽然知道意思,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词翻译合适,怎么想也想不出来。我就告诉他们平时要多积累。”“也有的学生问,成功有没有捷径呢?我说,从翻译来说,恐怕是勤奋了。”
尽管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的翻译生涯,但在国内的日语翻译界,竺家荣依然算是新生代。上一代的老翻译家刚刚退出,竺家荣这一代五六十岁的译者升格为日语翻译界的中流砥柱。她说,文学翻译不同于非文学翻译,对译者的要求很高,只有不断磨练才能保证翻译的水准,而自己还远远没有达到前辈译者的高度。她希望有更多有志于翻译的年轻学者能够加入进来。
“我40多岁才涉足翻译,说明只要起步就不晚。”

界面文化:你最喜欢的翻译家前辈是谁?
竺家荣:喜欢的翻译家很多,尤其是周作人、楼适夷、丰子恺等老一代翻译家的严谨、博学,给我们后辈译者树立了学习的楷模。特别是周作人翻译的《枕草子》,将他的日文汉文功底、日本文化的熏陶、对译作韵味的卓越驾驭能力展示得淋漓尽致。读来飘逸洒脱,不见雕琢的痕迹。钱理群曾说“在翻译史上,译作能够自成独立的艺术世界的翻译家是不多的,周作人便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深以为然。
界面文化:你认为翻译应该侧重直译还是意译?
竺家荣:两种翻译策略应该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键是如何运用得当。我原则上以直译为主,能够保留的尽量保留原来的日式词语,如翻译渡边淳一《天上红莲》时,对里面的月份异称、古代日本地名、古代日本官职、古代日本服饰和器物名称等等都尽量保留原语,让读者更多地接触到日本古代的文化气息。目的是尽可能传递异国风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其实意译主要涉及某些词语,如文化词语、惯用语、成语典故、佛语、词曲名称等,如果是中国人也能理解的,我便直接拿来用,如果不能理解,宁肯采用注释方法,最后才考虑对译或意译。因此我的译作,注释往往比较多。因为总觉得有些词,即便意译也是不能够达意的。
例如“增上慢”这个佛语,中文里虽然也有,但一般人不知其意,很多译者都意译为“狂妄傲慢”,但似乎并不能确切传达其意,也与文脉不贴合,我采用了直译加注释,觉得这样既可保留这一佛语,也比较贴近原意。再比如日语惯用语“追二兔不得一兔”,“猴子也会从树上掉下来”,很生动有趣,国人也能明白,就直接拿来用,没有对译为“鸡飞蛋打”和“好马也有失蹄的时候”,但是“做三天和尚”,中国人就看不懂了,就必须对译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总之,尽可能兼顾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应该是作为跨文化桥梁的文学翻译努力的方向。当然,翻译没有绝对的标准,怎样翻译更好,有待实践的检验。
界面文化:你现在最想翻译的作品是?
竺家荣:很想翻译樋口一叶,但是几次机会都由于种种原因错过了,很有些遗憾。希望以后还有缘分可以翻译她。
界面文化:当一部作品出来时,你是否心惊胆战有人来挑错?
竺家荣:对我来说,或许换个说法比较好,就是敬畏读者。因为,译者以及出版社虽然努力忠实原作,多次校对,但毕竟会有一定比例的误译、漏译或不完美,读者挑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都希望看到完美的译作。译者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给出版社再版时修改,是责无旁贷的。大多数读者都是非常善意地提出问题,很感谢他们。即便是不那么正确的意见,也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读者的鞭策可以不断地给译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尽可能减少失误的比例。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翻译也应该拿版税而非千字多少元的稿费?
竺家荣:我从来没有拿过版税,一直是拿稿酬。恐怕对于出版社来说,译者和作者的情况不一样,给译者付稿酬更合理吧。
界面文化:你认为稿酬多少才合理?
竺家荣:稿酬的问题自然也是市场决定的。我曾经和某出版社总编聊天,他说我们不注重译者的名气,尤其是一些通俗文学,或非经典作品,难度不太高,一般译者可以胜任。我觉得,出版社这样做自然是有道理的。当然,也有一些出版社很关注市场定位,以精品图书为目标,确保出书质量上档次,因此会适当增加些稿酬,推出名家名译,从性价比考虑也是比较划算的,可以细水长流等等。
从文学翻译者的角度说,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自然希望多争取一些稿酬,但是,举凡进了这个门的人,图的就不是稿酬多少了,若要图稿酬的话,就去翻译其他稿酬高的专业资料了,或者干脆干别的了。从我来说,稿酬虽不多,但译作出版后,上面有译者的名字,并且会一直存在下去,这个署名权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部分隐性报酬。至于说多少合理,只能说存在即合理。
界面文化:你对当今电子词典、网络资料运用的看法?
竺家荣:当然非常有用。快捷,准确,信息量大,好处多多。有时候虽然找不到准确的译词,但是通过看图,就可以大致翻译出来了。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现在翻译正在分化为流行文化、纯文化、官方用语等多种体系?
竺家荣:翻译者只是将作品的语言转换为另一国语,没有权力改写为流行文化色彩或纯文化色彩的作品。也就是说,作品本身属于什么体系,译作就应该是什么体系的。比如说,纯文学作品,不可能译成大众口味的作品,那样一来,就是不忠实原作,因为风格改变了,就好比把人画成了漫画。译者可以加工的,恐怕只是在文体的选择或词语的雅俗选择上。
随着时代的发展,词语会有相应的变化。比如谷崎润一郎等明治大正时代的作品,老一辈译者由于他们的文学素养与生活的时代等因素,翻译得比较偏半文言或白话文,但现在的译者则是现代口语文体和白话文的杂糅感。冗长的句式也逐渐在变短。总之翻译腔相对减少,这可以说是与时俱进。不过,我的原则是尽可能不使用网络语或还未定型的流行语,以及脏话、俚语等,保持语言的纯净。即便要翻译得通俗易懂,但在修辞方面,仍尽量选择贴近作品语境的词汇,努力再现原作的氛围。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的相互渗透虽是必然趋势,但是文学经典则是经历岁月的磨砺而历久弥新,沉淀于民族文化的底层,不断焕发光彩的。
界面文化:你怎么解决外来词汇的中文化问题,是不是有事不得已需要自己制造新词?
竺家荣:上面第2题也涉及了一些,我一般能拿来就拿来用,一方面可以丰富中国语的词汇,二来可以增添新奇感,有益无害。由于胆子小,自己很少造词,当然,《一个人的好天气》新造了个“飞特族”,不过,那是出版社造的。以后有机会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失乐园》(渡边淳一)

竺家荣:《失乐园》是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也是日本当代文学在中国影响持久而广泛的名作之一,20年来长销不衰。很多和我年龄相仿的中老年人,当年大多看过或是听说过这本书。由于该作品内容涉及人们非常敏感的情爱问题,初版不得不做了删减,直到十二年后全译本面世,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包容度与出版状况的变迁。渡边淳一文笔细腻唯美,善于营造浪漫气氛,很有日本文学的特点。特别体现在对于两性关系、性心理等最隐秘层面进行的淋漓尽致的描绘,以及精彩的夹叙夹议等将陷入婚外情的男人女人的困惑、挣扎、欢愉、无奈、孤独、贪求等都曝光于笔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发源于《源氏物语》的日本审美传统。对于开启中国读者对日本文化了解的窗口,可以说很有价值。对我而言,第一本译著就有幸遇到了《失乐园》,从此走上了译介日本文学的漫长道路。
《一个人的好天气》(青山七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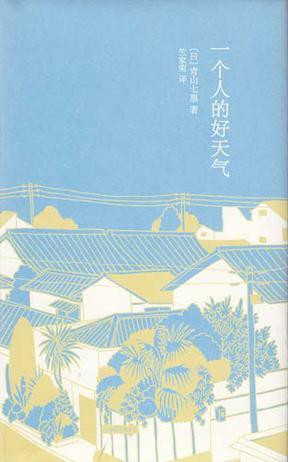
竺家荣: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推出获得芥川奖的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以及后来陆续出版的七惠的《窗灯》《温柔的叹息》《碎片》等,在译介文学市场中掀起了一股日本青春文学的冲击波。这位80后作者描写了一个飞特族(以打工为生)女孩子的感情生活,尽管情节平淡无奇,却以其淡然洒脱的独特韵味牵动着读者的心,深受好评。一出版,便十分畅销,可以说影响了80后乃至90后一代人。而且至今仍然不断加印,创造了出版界的一个传奇。该书还有一个特点便是独特的装帧。三层雅致的色纸,每层露出一点边,犹如日本古代和服十二单露出衣袖层层那样的唯美。可以说,准确的市场定位,精美的装帧,不遗余力的宣传等助推了此书的畅销。在日本默默无闻的青山七惠,在中国成为相当知名的日本作家。迄今为止,她的每本书都翻译到了中国。其中本人翻译了她的10部作品。由于年龄上的差距,对于我来说,在处理词汇,营造年轻人的感觉上的确下了一番工夫。译作能够得到广大年轻读者的喜欢,作为译者是最幸福的事情。
春琴抄(割芦·吉野葛)(谷崎润一郎)

竺家荣:2016年翻译出版的《春琴抄》是日本唯美大师谷崎润一郎最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在日本多次搬上银幕。《春琴抄》生动细腻地描写了盲女琴师春琴与仆人佐助之间既是师徒又是恋人的一世情缘。当春琴被毁容后,佐助毅然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使自己处于与春琴同样的境遇里,将师傅的美貌永远定格在了自己的记忆中。小说结尾通过禅师之口肯定了此举“转瞬之间断绝内外、化丑为美的禅机”,充分揭示了谷崎文学追求“永恒的女性”的一贯主题。
能够翻译这样的名篇以及另外两篇很有翻译难度的短篇,甚感荣幸。虽然以前也翻译过谷崎的《钥匙》等4部作品,但时隔多年,翻译的水准比当年有所提升,20年来的翻译实践的积累,以及对于谷崎唯美主题的理解,及其优雅文体的认识,使自己可以比较有自信的驾驭有一定难度的《春琴抄》。此外书的装帧也很独到。没有花哨的人物,樱花色的封面上只有象征琴弦的“春琴抄”三个字,日本味十足。里面的精装本封面右上角,还有盲人点字的书名,极为精致有趣。一方面也反映出当今中国的出版界,正在向着追求高品质图书的目标努力,从这本《春琴抄》可以窥见一斑。
1981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长期从事日本文学、翻译的教学、研究与译介,现为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翻译专业的硕士生导师。主要代表译作有:失乐园(渡辺淳一)、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村上龙)、晓寺(三岛由纪夫)、京洛四季――美之旅(东山魁夷)、被偷换的孩子(大江健三郎)、一个人的好天气(青山七惠)、人间失格(太宰治)、心(夏目漱石)、春琴抄(谷崎润一郎)等。
(文中所有竺家荣图片来自界面摄影记者吕萌)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