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然位于性革命余晖的延长线上并受其影响。回看这一历程,或许有助于厘清我们今日在性方面仍未解开的难题。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如果说性是中国人难以避开的话题,那么潘绥铭就是中国性社会学无法绕过的名字。在他做过的调研中,以“红灯区”研究最为引人注目,实际上,其研究范围要远大于此,几乎涵盖了中国40年性革命以来所有与性相关的所有议题,他也被同仁们称为“性学教父”,而这些研究也都被记录在了新近出版的《风痕》这本学术性自传中。

潘绥铭认为,如今中国的性话题愈加弥散化和炫彩化,性革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敌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他也是时候退休了。潘绥铭和团队成员曾经在2000年至2015年完成了四次“全国总人口性调查”的壮举,按说2020年应该继续,然而中国的性化在2015年达到顶峰,随后便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不确定性。另外的原因是,当社会传播更迅猛,社会氛围更苛刻,不敢真实回答的人数就会增加;其次,随着城市居住区越来越封闭,农村家庭越来越空巢化,随机抽样也会更难。令潘绥铭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选择也歪打正着地避开了新冠疫情。
种种迹象表明,属于潘绥铭和他的性社会学时代已经过去了,无论是“红灯区”还是“包二奶”,这些名词也已经不再常用。但事实上,我们仍然位于性革命余晖的延长线上并受其影响。回看这一历程,或许有助于厘清我们今日在性方面仍未解开的难题。

在上世纪90年代,潘绥铭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性革命,这场革命并不是紧随1979年的改革开放发生的,而是经过文革后的过渡恢复期,迟至1985年城市经济改革才出现。当一切以经济为中心,单位就不再管男女之事,人口流动加剧,私人空间扩大,这些都有利于性革命的出现。虽然彼时还有与性相关的法律,但是在潘绥铭看来,“讲法制”恰恰是唯道德论开始失效的表现。他在《风痕》中提到这样一则逸闻,原文如下:1984年,居委会来捉奸,对方却撕下法制教育课本的其中一页从门口递出来,上面写着:“拿搜查证来”。
1980年,对1950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进行了修正,将“夫妻感情破裂”明确列为离婚的法定理由,这一修正冲击了婚姻神话,确认了爱情的优先地位。同年还上映了贡献出中国影史第一吻的电影《庐山恋》。社会学家潘光旦1946年编译的《性心理学》一书于1986年再版时,费孝通在后记中写道:“中国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局面正在通过开放和改革向现代社会转变……’两性之学‘将能得到坦率和热情的接受。” 这便是潘绥铭的学术研究起步时的背景,站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要如何理解此后的性革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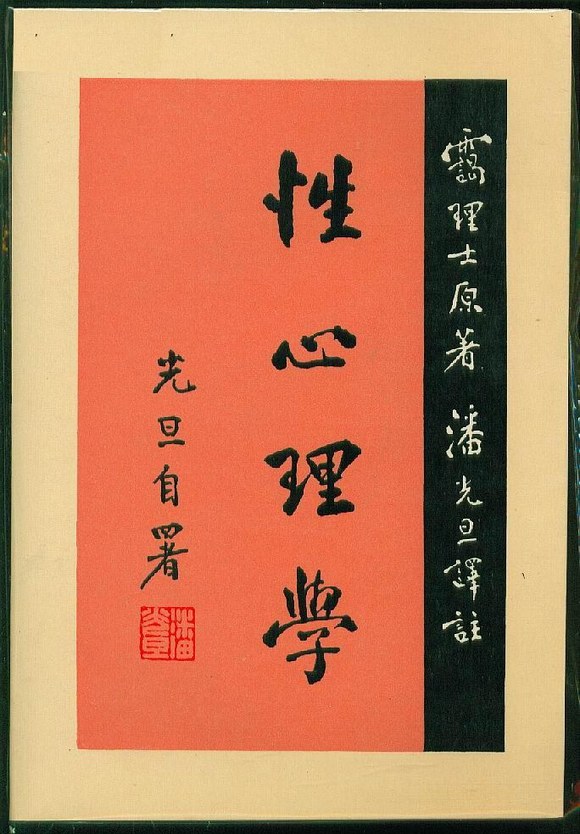
在书中,潘绥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说独生子女政策是性革命之母,那么文革就是性革命之父。
前者相对容易理解,当夫妻生完第一个孩子,用着避孕工具的性生活就不再是为了生殖,而是纯粹的寻欢作乐了,“性的快乐主义”第一次在主张传宗接代的中国有了发展的可能。但是实现这一点也有其前提,在文革时期,对于性快乐的禁止以及生殖目标的追求,反而造成了人口出生的高峰。到了1980年代,文革中出生的人正好进入青春期,而他们势必会发展出自己的文化。所以,中国性革命的一大现象便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再教育和文化反哺,黄昏恋、广场舞等“老来俏”活动的流行便是最好的例证。另外,中老年人在性观念上的缺失,也倒逼出了1985年之后社会化性教育的出现。

另一方面,独生子女政策也产生了其他后果,也就是潘绥铭命名的“单性别成长”,独生子女没有异性兄弟姐妹,无从了解异性世界的奥秘,所以从传统视角来看,他们在性爱婚方面都出现了困难;以新视角来看,则是变得更加独立自主了。如今,90后的性欲减低、性生活降级是一个媒体经常谈论的问题,性冷淡的情况更集中在高学历人群中,这一点也在潘绥铭的大学生性调查中得到了印证:在进入21世纪后,大学生的性行为开始剧增,但是在1991-2015年七次全国大学生之性的调查中,大学生发生过性关系的比例都低于全国同年龄(18-23岁)的人口。
如果按照以上观点,中国的性革命与西方并没有本质区别,毕竟,人口爆炸带来的性文化活跃在60年代的欧洲就已经发生过了。然而潘绥铭认为,中国的性革命远非西方的翻版,而是有许多本土化的情境,传统习惯和概念也一直在发挥着作用。
出版于2013年、潘绥铭与黄盈盈合著的《性之变 : 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一书就曾提到,中国的男女青年在找对象时,相当多的人相信的既不是传统相亲,也不是美国式个人奋斗,而是可遇不可求的“缘分”,因此,他们在发起恋爱关系时,往往“既不主动也不被动,既不积极也不消极”,可以说位于两者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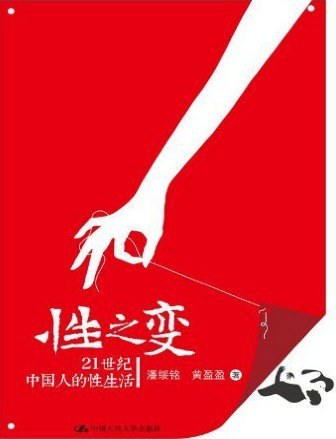
另一个仍在影响国人的观念是“恩爱”。西方社会的性关系以个人权利为基础、崇尚激情和精神交流,中国人却难以脱离亲情与关系社会,更讲究夫妻恩爱,而恩爱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无法被精确翻译。即使中国的情侣是从浪漫爱开始,也要最终走进夫妻恩爱,并通过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来维系这种恩爱,“柴米夫妻,爱不爱的没那么重要”。
潘绥铭发现,由于我们追求的并非随时离婚解约的“一次式专偶制”,而仍然是白头偕老,所以当今中国的婚外恋比例甚至比某些发达国家还要高。这一点也体现在了婚姻法上:1980年修正的《婚姻法》首次明确规定了离婚的唯一标准是双方感情破裂,这也助力了性革命的发展;同时,独生子女政策也对离婚率产生了影响,孩子的减少使夫妻之间养育合作的时期极大缩减,离婚时对子女的顾虑也就减弱了。然而,2000年再次修正的《婚姻法》恢复了“有条件离婚”的理念,这在潘绥铭看来是不进反退、值得批评的表现。在他看来,中国的婚姻革命是落后于性革命的发展的。

不过,中西性革命的最大区别其实在于,现代西方是在自由社会中发起性革命的,中国人则需要在体制中不断地打擦边球。这形成了十分矛盾的局面,一方面,中国人的性史无前例地没人管了;另一方面,关于性和隐私却有着五花八门的公开干涉与管制。
于是,性革命在中国的表现就并不是与性有关的法律的修改,而是“性法律”的执行力度越来越小,乃至形同虚设。然而,文革中的精神禁欲主义却仍然对社会施加着影响,它在1989年变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了21世纪初缩减为讲礼貌运动,其社会诉求已经降低到起码的人际关系层次,来顺应“中国不能乱”的社会需求。
这促使潘绥铭在引进西方知识理论的同时,也在努力宣讲中国的性现状与欧美的差异。在他看来,福柯这样的后现代理论家固然伟大,但前提是在他身处的社会中,话语和符号比政府的作用要大。而在中国,诸如“夫妻性生活”这样的说法并不是话语符号,而是上级规定的用词,也就是赤裸裸的权力。“如果按照话语理论来分析中国传媒上说的代表什么,那就是假装老外。”这也是为什么,和福柯比起来,潘绥铭认为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把性放在关系视角下,对国人来说更具有真实感。吉登斯的著书在中国也曾经引起过很大的反响,比如那本《亲密关系的变革 : 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
正如前文所说,中国的性革命既有独生子女政策等性制度管控,也与西方的性革命有着重要区别,中国的性社会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我们要如何定位这样的性社会学呢?
潘绥铭借用了《三国演义》内容,提出这样的观点:从社会结构来看,最强大的社会势力是曹操,也就是性制度的管控;与之抗衡的是民间争取权利的力量,以及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和“客观测定”的方法,可以说是孙权;潘提倡的性社会学则处于刘备的位置上,既要与孙权站在一起,也要直言不讳地批评孙权在方法上的失误,致力于在性研究这一方小小的时空“染上属于我们的色彩”。
回看潘绥铭与性社会学相互构建的一生,能够看出他寻求儒家中庸、调和精神的倾向,这一点也体现在了他的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对英文中“sexuality”一词的引介,sexuality包括一切与性的情感、价值、态度有关的表现。在汉语中,“性”却仅指身体行动,不包括情感和心理的内容。那么,是应该发展本国语言跟上世界学术发展,还是避免生搬硬套外来词语?在2006年的国际研讨会上,潘绥铭和与会者达成共识:沿用“性”的译法,但要争取让国人理解“性”字的全新含义。

另一个凸显其平衡精神的例子,是潘绥铭和黄盈盈提出的“主体建构”研究视角。由于性活动存在于关系中,并且极为主观,所以研究者不应该承认一个“纯粹主体”,也不应该猜测对方,而是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让对方充分呈现自己。如此一来,许多现象都能够得到解释,比如即使双方进行了性行为,但是行为只能算到有性反应的那一方(往往是男性)头上,所以强奸不是性,卖淫也不是性。
主体建构的理论来源是现象学,它不追求因果,因为不是所有行为都有终极的原因。这与中国的阴阳思想是相似的,事实上,晚年的潘绥铭也逐渐开始认为,阴阳哲学并非西方社会性别理论的敌人,而应该是促进后者进步的思想源泉。sex在拉丁文中意味着两性的分开,但阴阳讲究合在一起,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社会性别之间的争斗原本就是荒谬的。
然而,认识到以上这些也花费了潘绥铭漫长的岁月。80年代是西方的社会性别(gender)理论传入中国的时期,潘绥铭也在1985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开设了“外国性观念发展史”课程,此举震惊了全校,标志着其性社会学研究生涯的开始。此后,潘绥铭摸着石头过河,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这促使他反思西来理论,对本土情况进行了充分思考。1986年,潘绥铭第一次尝试问卷调查,但是由于对社会学方法不熟悉,加之印刷技术有限,调查最终失败。此后,潘绥铭还用台式电脑跟着朋友学习定量统计方法,然而苦于调查没有国家或政府的资助,研究主题又是“性”,所以很难找到发表平台。
潘绥铭在书中如此总结道:在中国,研究性的人是孤独的。性是社会的孤儿,性研究就是弃儿。“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实行天罗地网般严密行政管理的社会中,居然没有任何机构来领导和管理性”,这既是性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但是反过来,性研究也就没有获取行政与学术资源的渠道。其结果就是,虽然21世纪以来中国的性研究者越来越多,但仍很难像其他学科那样形成大规模的共同体,由于课题特殊,研究者往往还要搭上自己的全部人格。

在《风痕》中,潘绥铭还谈到两个事例,它们既说明了性社会学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的尴尬位置,也与性革命本身产生了有趣的交叉。1988年,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开设了“性科学培训班”,招收全国计生委的干部来培训,然而其目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在城市经济改革兴起之际,利用培训为社会学系“创收”,为教师谋福利。学员也只是想用公款出差旅游,作为对此前清教徒生活方式的补偿。在1999年的某次培训中,计生委的干部看着前来上课的潘绥铭,“笑而不语,目光中流露出慈母般的怜悯”。
另一件事发生在21世纪初,潘绥铭受邀给名为“商界女精英提高班”的“富婆”们上课,其中既有公司女高管也有前来打发时间的商人老婆。他习惯性地讲起了社会性别理论和一点女性主义皮毛,引得听众一片哗然。可是,这样没有性别觉悟的女性,却强烈要求听到“能够留住老公的心”的性技巧。潘绥铭总结道,中国的性革命虽然值得肯定,却也存在包二奶、傍大款等向传统社会的逆行,并且缺少了社会性别的革命(包括男性进步、同性恋平权),以及女性的性革命。
当然,站在今天来看,女性对于性权利的要求已经提上了日程,潘绥铭也穷尽一生的研究成果实现了“功成身退”,性社会学不再那么遭人非议了。然而,不管是相对于性革命滞后的婚姻观念,还是对于性既无根据也无逻辑的管制,书中写到的种种现象却仍不免让人感到熟悉,也不时提醒着我们,在这个看似对于性已经没有太多禁忌的社会,我们还缺少什么,还需要继续争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