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就像对待一件玉器,需要耐心细致地不断打磨。”

《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中文简体版首发式在北京一个院落深处的小剧场里举行,许多身披巫师袍、手拿魔杖的人进进出出,从七八岁的孩子到中年不等,气氛像是一个酝酿已久的节日。当主持人报出译者马爱农的名字时,台下爆发出一阵掌声与欢呼,等了片刻,马爱农从台侧一个隐匿的角落里探出身子,轻盈而羞涩地跨上了台,神态和眼睛里的光芒像是一个小女生。
“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我不是很会说话,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属于我们哈迷自己的盛大节日,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几句。”马爱农一手持着话筒,一手拿着魔杖,声音也很年轻,甜甜的。16年前,“哈利·波特”初次进入中国,在一代年轻读者的世界里搭建起了一座“魔法的城堡”,马爱农作为译者之一功不可没。“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隐秘的精神世界可以安放我们对奇迹和魔法的想象和渴望,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觉得有了这个世界的存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铠甲护身,呼神护卫,逢凶化吉,所向披靡。”16年过去了,当年的孩子们纷纷长大成人,而马爱农似乎真的有了魔法护身,看起来始终年轻得像个女孩。

在北京朝阳门内大街喧嚣而宽阔的马路边,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在的这座灰白色的五层小楼毫不起眼。拾级而上推门进去,泛黄的墙壁、绿色的墙漆、木制的老旧桌椅,它几乎保留着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社刚刚迁到这里时的样子。马爱农的办公室在这栋楼的四层,阳光从窗中照进来,让屋子的色调有些泛黄,一摞摞书堆得到处都是,整个房间除了一个书桌和两个小沙发,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的空间。
在几册《哈利·波特》的封面上,马爱农和妹妹马爱新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在译林出版社的另外一个办公室里,妹妹马爱新也在做着相似的工作。马爱农的父母也是编辑,而祖父马清槐是一位英语老翻译家,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参与过建国以来一系列政治、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长大,马爱农从中学时代起就喜欢读英语文学原著,并且对中英文之间的翻译感兴趣。
第一次完整地译书是在大学毕业那年,马爱农翻译了儿童文学作品《绿山墙的安妮》,这部“处女作”缘起于大学的一份作业。马爱农在南京大学英文系读书,大四那年的编辑课,老师给大家留的作业是报一个图书选题。马爱农那年正好读到了英文版的《绿山墙的安妮》,“我非常喜欢那本书,觉得书中安妮这个形象塑造得特别灵动、有活力,充满了想象”,于是她选了这本书作为选题,详细地陈述了它的出版价值。这次练习式的作业被付诸了实践,老师真的联系了出版社,出版社决定引进这本书,翻译的任务就交给了马爱农。
大学毕业那年暑假的三个月时间里,马爱农整个儿用来翻译《绿山墙的安妮》。祖父听闻这个消息,专程从北京赶到南京,指导孙女的翻译。那时候没有电脑,马爱农在稿纸上翻译,译完一部分交给祖父,祖父就逐字逐句地在稿纸上为她改一部分,之后马爱农再拿回来重新抄写一遍。马爱农由此得到了人生中翻译“启蒙的培养”,如何转换中英文的句子结构、如何摆脱翻译腔,祖父不曾给她讲理论,而是在这样的实践中把翻译技巧一点点地传授给了她。
大学毕业后马爱农到南京医科大学做了英语老师,但是她觉得教书不太适合自己。“我不是很擅长口头表达,也不擅长当别人的老师,还是更喜欢案头工作,喜欢跟稿子打交道,喜欢自己独立安静地做事情。”四年后她离开了教师的职位,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了研究生,专业是翻译理论与实践。
研究生毕业后,马爱农没有再做其他的选择,直接来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外国文学编辑室全心全意地做起了一名编辑。调研国外的出版物,组织译者翻译,再逐字逐句地修改加工译文,这样的工作符合她的理想:安静、独立、每日和稿子打交道。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工作室有20多个人,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甚至阿拉伯文、越南文等各语种的专家汇聚一堂,包括孙绳武、蒋路、卢永福等翻译界前辈,他们编译出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代的一系列外国经典名著。无论是编辑修改译文的日常工作,还是开会时前辈翻译家的讨论,马爱农默默地从中为自己的翻译汲取营养。

自翻译《绿山墙的安妮》之后,马爱农一直用读书和工作的业余时间来做文学翻译。《绿野仙踪》、《彼得·潘》、《小王子》,还有种种经典的和当代的儿童文学作品,马爱农对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情有独钟。小时候,马爱农喜欢读《木偶奇遇记》、《汤姆·索亚历险记》,还有任溶溶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即使成年后接触了无数中外文学作品,她最喜欢读的还是儿童文学。“就是对儿童文学更有感觉一点,”她睁着大眼睛没有过多解释,仿佛这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自己也很难用语言形容。
成人文学作品马爱农也翻译过不少,有出版社来找她翻译,她也会接下来,其中也包括一些沉重的东西。她翻译过“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威廉·巴勒斯的《裸体午餐》,这本书里有很多“晦涩、阴暗、病态的东西”,它与马爱农所习惯、欣赏的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马爱农费力地寻找与作者之间的平衡,试图进入作者的感受,“但是那种感受我不喜欢,也好像很久都没办法进入,所以翻译那本书很痛苦”。还有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集,也在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黑暗,马爱农认为写得很有深度。但她还是更喜欢儿童文学带给自己的感觉,“儿童文学能带给我比较轻快的心情,那种感觉让我很开心”。
自己翻译的成人文学中,马爱农比较喜欢的是安妮·普鲁的《船讯》,还有几位爱尔兰作家的短篇小说。“我比较喜欢接近人的原始状态的风格,”马爱农说,“就是指人的自然特性,比如爱尔兰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加接近人的本质的国家,作品也更加接近人的本质,生活的本质。”而《船讯》的故事发生在刮着极地风暴,弥漫着咸腥味的纽芬兰岛上,马爱农在译后记中写道:“在纽芬兰粗糙的海岸上,人是被海、被风、被冰山包围着的人,他们不是用理智,而是用直觉去感悟和体验自然界的潮涨潮落、阴晴圆缺。他们与自然融为一体,共同形成一种奇特的生存氛围。”
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买进了《哈利·波特》系列前三本的版权,那时《哈利·波特》虽然还没有风靡全球,但在国外已经是畅销书了。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最早的译者是那时已经70岁高龄的老翻译家曹苏玲,但她那时对这种风格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太能接受”,觉得里面的魔法、奇幻世界会“鼓励小孩子去想入非非”,再加上年龄原因,曹苏玲翻译了半本书就不再继续了。由于马爱农和马爱新已经翻译过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把翻译《哈利·波特》的任务交给了姐妹俩。
马爱农拿到《哈利·波特》非常喜欢,觉得很新奇,跟她以前看到的国内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都不太一样。“它完全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对这个世界的架构完整丰满,故事的想象空间很大,它吸引我的还有它的幽默,虽然其中有邪恶的地方,但是隔一段内容就会有让人发笑的妙笔。”
曹苏玲前半本的翻译奠定了基调,她的译文现在还保留着,之后马爱农姐妹翻译的部分沿用了曹苏玲翻译的所有人名物名。马爱农和马爱新分工,每人翻译一部分,马爱农再完整地看一遍,把相差大的部分调整一下,责任编辑王瑞琴等人再最后统一整体风格。
翻译《哈利·波特》是一个不断得到惊喜的过程,“每次拿到新书的时候都会觉得,哟,她又想象出了这么多新东西!有些故事发展和人物发展是我原先完全没有想到的,好像它不断在拓宽这个想象的世界”。翻译前三本的时候,马爱农以为这只是一个校园生活的故事,一所魔法学校,几个孩子的冒险,从第四本开始,一下子出现了魁地奇世界杯、魔法部、傲罗、另外几个魔法学校……魔法世界的版图不断地开拓。“这套书是一个成长的作品。”马爱农说。前三本仿佛还属于儿童文学,但几年过去,随着主人公从11岁长到17岁,书也在成长,基调慢慢变得沉重,逐渐不再属于儿童文学,而与此同时,读者可能也已经由一个儿童长成了青年。
和所有的哈迷一样,每年《哈利·波特》出新书的日子,对于马爱农也是一个节日,她也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后面发生了什么。拿到新书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会让马爱农先放下社里其他的项目,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回家专心翻译。“不会紧张,也没什么压力,时间肯定是有些仓促的,如果时间多一点我们会翻得更好一些,但这个时间并没有超越极限,也是可以接受的。”
罗琳的文字不难,唯一容易卡住的地方就是一些译名如何确定,那些咒语、神奇动物、魔法界的器物,都是罗琳自己想象出来的,字典里查不到,翻译也只能靠想象。英文版的咒语通常是拉丁文词根加上一些念起来比较有力的音符,翻译过来既要表达出词根的意思,又要让咒语念起来铿锵有力。此外,书中借鉴了很多西方经典的神话传说、巫师文学、炼金术历史,这些都是马爱农之前在阅读欧洲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时就接触过的。

在哈利·波特三人小组中,马爱农最喜欢的其实是罗恩。哈利固然有很多可贵的品质,但他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些紧急关头总会被赋予超出他年龄的智慧和勇气,会让人感到有些失真。罗恩的形象相比起来更加亲切自然,符合大部分男孩成长中的体验。赫敏在马爱农的眼里也不是特别可爱,偶尔有些教条主义,还有些武断。“生活中我也不是很喜欢‘学霸’那种特别看重书本知识的行为方式。”马爱农笑道。至于哈利和金妮的感情,马爱农也是慢慢接受的,并逐渐喜欢上金妮,发现她“很有幽默感,还有一种处理事情举重若轻的可贵性格”。
《哈利·波特》系列的终结对于这一代许多人来说仿佛意味着童年的终结,当《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的故事结束,马爱农也怅然若失。多少哈迷为那些陪伴过哈利的人物的死去流下过眼泪,邓布利多、疯眼汉穆迪、卢平、斯内普教授……而最让马爱农难过的是弗雷德·韦斯莱的去世,这对一直在制造欢乐的双胞胎兄弟只剩下了一个,还有哈利的猫头鹰海德薇被杀死时,马爱农也十分痛心。“人物都是罗琳创造的,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处置,我们只能接受她的安排。”
“翻译《哈利·波特》跟别的书不一样,文学翻译是一种幕后工作,多半是默默无闻地完成,但这本书因为超级畅销,所以使译者也变成了公众人物。”在哈利·波特的主题活动上,马爱农的出场会伴着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哈迷们会给马爱农讲《哈利·波特》如何伴随自己成长,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感到很有成就感,可能比翻译别的书更有成就感一点,因为自己能够加入到把这套书带到中国来的工程当中。好多哈迷对这本书真的有非常深切的感情,我经常被他们的肺腑之言所感动。”这些体验是翻译其他作品不曾获得的。
相隔九年之后,《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于今年问世了,尽管它不是罗琳主笔,而且只是一个舞台剧的剧本,但它毕竟是罗琳本人唯一钦点过的“哈利·波特8”。马爱农依然承担了这本书的翻译,“本来以为七本书结束哈利·波特的故事就终结了,不会再有关于它的任何作品,所以这次能够看到这个剧本,知道那个神奇的魔法世界还在继续,我觉得非常高兴。”
然而“哈8”出版后有一些哈迷表示失望,“这也是正常的,读者习惯了前面几本《哈利·波特》的那种阅读体验,”马爱农说。“哈8跟前面几本确实不一样,它是剧本,体裁不一样,描写方式也不一样,它的人物设置的关注点跟原先也不太一样。原先关注的是魔法世界与伏地魔的抗争,这部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亲子关系和时空穿越这两大主题上,而且依然不失幽默。我觉得也很好看。”
现在马爱农正在做7本《哈利·波特》的修订,已经进行到最后一本。翻译到后面几部时,她发现前几部的翻译中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伏笔。除此之外,还想把文字修改得更符合中文语感,让读者读起来更流畅一些。“既然有那么多人喜欢,就尽量把它做得再好一点,翻译就像对待一件玉器,需要耐心细致地不断打磨。这次争取把以前的缺憾弥补一下。”马爱农相信,这套书是能够作为经典留存下去的。
《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简体中文版上市前一个月,一些网站已经有标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文译本销售。“那本书根本不是正规出版物,是某个地下印刷厂制作的,书号和版权页全都是假的。”提起来马爱农有些气愤。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此专门发布了一份声明,“要求这些网站立即停止销售这种非法出版物,并将进一步追究这些网站和非法销售者的法律责任”,令各网站上这本书全面下架。
自《哈利·波特》在国内畅销以来,这套书的盗版和网络译本层出不穷。“网络译本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是很多哈迷自发完成的,凭着对《哈利·波特》的一股热情。但是它不能传播,因为没有得到正规授权。”马爱农知道曾经有一个法国人私自把《哈利·波特》翻译成法文,在网站上传播,受到了起诉。“在国内尚未有人起诉这些网络译文,但是深究起来也是不合法的,做成盗版书就更是违法行为,是非法盈利了。”马爱农说。
国内出版界的现状是,文学作品原著者要维护自己的权益都困难重重,译者的权益就更难了。几乎没有译者会主动维护自己的法律权益,但马爱农站了出来,一口气打了两个官司。
2014年,马爱农在书店里偶然看到了一本跟自己的版本装帧设计几乎一样的《绿山墙的安妮》,她拿起书来翻了翻目录,发现目录跟自己翻译的只字不差,再翻开里面的内容,也几乎是一模一样。“尤其是里面的诗歌,按说诗歌的翻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译法,特别能够体现个性的差异,可是这位‘译者’的诗歌也翻译得跟我完全一样,一个字都不差。”马爱农把这本书拿回出版社,交给了校对科,经过对比和统计,发现这本中国妇女出版社版出版的署名“周黎”的《绿山墙的安妮》,文字97%与马爱农译本相同。
相隔不久的某一天,一个朋友来访时,说自己在书店里看到了马爱农翻译的一大套书。马爱农觉得很奇怪,上网查了一下,发现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包括《马克·吐温小说大全集》《一千零一夜》《兔子坡、大象巴巴故事全集》等13本,署名为“马爱侬”。马爱农去书店买了几本,发觉这套书翻译质量低劣,多半是从各种译本抄袭拼凑而成,最后盗用了自己的名字,实在令她难以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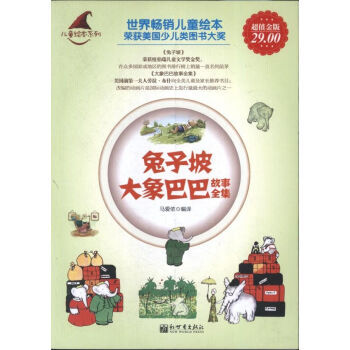
两件事情放到一起,马爱农决定起诉。“其实我也不想起诉,因为太耗费时间和精力了,但是我在做编辑工作的过程中,经常有一些译者跟我反映有别的出版社出的译本跟他们翻译的很像,大段地抄了他们的文字,但是他们也都选择忍气吞声,因为文学翻译者大都属于性格比较安静,与世无争的那种。我觉得我的这两个案例很具有代表性,抄袭这么明显,不妨好好地打一场官司,替长期受到侵权的译者同仁们出出气。”人民文学出版社很支持马爱农打官司,两个案子一起召开了记者发布会,请了出版社的法律顾问来做律师。译界听闻这件事也鼎力支持,《中华读书报》上发起了一个百人签名,全国各地的一百位译者,包括屠岸、柳鸣九这样有名望的老译者,都签名声援马爱农,“因为觉得出版界、翻译界风气太坏了,这种盗版现象太多了”。
两个官司告的都是出版社,实际上在背后操刀这些伪劣图书的是策划书籍的文化公司。中国妇女出版社版本《绿山墙的安妮》出版方提出私了,“别起诉了,你们不就是想要点钱么。”新世界出版社方面则辩称,他们出版的13种图书的真正译者叫孙豆豆,是其合作的兴盛乐公司编译部负责人,马爱侬是孙豆豆的笔名。他们还提供了一份孙豆豆出具的《说明》:“‘马’是家父的属相,‘侬’是上海话‘你’。‘离家方知父母恩’,在京数年,深感远在家乡的父母对我的牵挂和幼时家父对我的文学启蒙,就取了‘马爱侬’这个笔名,意即‘爸爸爱我’。”但马爱农认为,这套书原著涉及英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一个译者不可能精通这么多门语言,出版社就是在利用马爱农这个名字来误导读者。
两个案子都胜诉了,但马爱农和她的支持者“也没有大获全胜的感觉,反而感到有些失望”。马爱农起诉时,要求两家出版社停止发行、出售相关图书,并分别索赔33万和50万元人民币。法院审理后判定,中国妇女出版社版、周黎翻译的《绿山墙的安妮》侵犯译者马爱农署名权、修改权、复制权及发行权,判决中国妇女出版社赔偿马爱农经济损失2.5万元,但对于马爱农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而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署名“马爱侬编译”的图书,被认为是“不正当竞争”,判定赔偿马爱农经济损失10万元,赔偿马爱农合理费用1.5万元。两个判决结果与马爱农的诉求相差甚远,马爱农有些无奈:“这个赔偿并没有触到他们的痛处,只是罚没了不当盈利。我觉得这个力度很轻,实际上没有对他们构成惩罚,起不到打击的作用。”
实际上,盗版和抄袭的现象在国内儿童文学翻译领域尤甚。一方面,马爱农认为,儿童文学市场比较抢手,需求量大,盈利多,大家都不想放弃这块“蛋糕”;另一方面,儿童文学的读者一般不太关注出版社和译者,尤其是一些小城市的家长,可能并不清楚哪个出版社好,哪个译本比较靠谱,只要书名是一样的,书价便宜点,他们就会买。
与译者权益相关的法律,国内也不够健全,可以说是无章可循,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也很犯难,即使制定了法律,实行起来也很困难。2001年马爱农曾陪新闻出版署官员参加在卢森堡召开的国际标准书号大会,大会主任质问中国代表团:为什么中国盗版这么严重,而政府不采取得力措施。“15年过去了,中国的盗版现象还是一样严重,好像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马爱农希望自己的案子能对完善国内相关法律起到推动作用,“如果把这两个案子作为典型案例,估计国家今后会完善这些法律。”
“现在好的译者很难找,愿意从事文学翻译的人越来越少了。”马爱农表情有些怅惘。 “由于稿费偏低,仅靠翻译完全不能谋生,一般从事文学翻译的都是出于真正的喜爱。”马爱农做外国文学的编辑,接触的译者大多数都是一些高校教师,还有一些六七十岁依然在做翻译的老译者,年轻人越来越少。“即使有年轻人想做,他们也没有时间,因为这个不是他们的正业,他们首先要保证他们的生活。”大多数翻译工作者仅凭着一腔热爱,但是在生存面前,热爱想转化为成果,面临着重重障碍。

界面文化:你最喜欢的一位翻译家前辈是谁?
马爱农: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二十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的编辑工作。这么多年来,接触过许多前辈译者的作品,如,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张谷若译哈代,杨绛译《名利场》,王永年译欧·亨利,屠岸译济慈,查良铮译《唐璜》,杨德豫译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我从每一位译者的作品中都得到过滋养和教益,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其中,屠岸、王永年、李文俊、文洁若等老师,我和他们都有过交往,令我深受感动并获益至今的,不仅是他们的文品,更有他们高洁的人品。
我最喜欢的儿童文学翻译家是任溶溶,我认为他是真正具有童心的一位作家和翻译家,他翻译的许多童书我都反复阅读过。另一位我喜欢的翻译家是语言大师赵元任,他翻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许多经典段落,尤其是那些诙谐的打油诗,我深为佩服,至今都能背诵出来。
界面文化:你认为翻译应该侧重直译还是意译?
马爱农:没有绝对的直译,也没有绝对的意译。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唯一的宗旨是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和精髓,让读者阅读译文时所获得的信息、风格、情绪、意境等等,与读者阅读原文时所获得的相同相等,或大致相同相等。不管直译还是意译,都是为这个唯一目的服务的。每一次翻译,都是一次出发和抵达,从纯粹的外文出发,经过斟酌、掂量、寻寻觅觅、“旬月踌躇”,抵达纯粹的中文。我认为,翻译腔和欧化句是要尽量避免的,如果这样的文字大量存在,译文只能是一种半成品,还停留在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的半路上,没有完成真正的抵达。
界面文化:你最想翻译的一部作品是?
马爱农:其实,如果时间精力允许的话,所有经典的英美儿童文学作品,我都愿意翻译。每翻译一部这样的作品,都是在经典中的一次完全浸泡,会获得比普通阅读更纯粹、更深刻的享受。
界面文化:当一部作品出来时,你是否心惊胆战有人来挑错?
马爱农:没有。翻译一部作品,心思应该完全在吃透原文、精确转换、打磨中文的过程中,可能不会有闲心去考虑这样的问题。译者会尽量要求自己全心全意地投入,认真翻译好每一段文字,做到问心无愧。
界面文化:你认为翻译是否也应该拿版税而非千字多少元的稿费?
马爱农:如果是非公版的图书,出版社已经为购买翻译版权支付了版税,再要付给译者版税就有一定的困难。
界面文化:你认为稿酬多少才合理?
马爱农:我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出版社的编辑,又是一位译者。我能理解出版社的难处,也能理解译者的不容易。一般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是真心热爱这项工作,能在翻译过程中获得大大超越金钱回报的精神享受。稿酬方面,只要双方能达成理解,彼此获得心理平衡,就是“愿打愿挨”的事。
界面文化:你对当今电子词典、网络资料运用的看法?
马爱农:用网络词典和网络资料代替纸质的大辞典和工具书,确实节省了许多时间精力。但翻译仅靠这些是不够的,尤其是文学翻译,更重要的是译者的文学素养和知识底蕴,以及对他国文化的熟悉程度和感悟能力。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现在翻译正在分化为流行文化、纯文化、官方用语等多种体系?
马爱农:翻译风格如何,是由原文风格所决定的。如果同一种风格的作品,为了迎合读者的需要,人为地把它们翻译成“流行文化、纯文化、官方用语”等不同风格,肯定避免不了对原文进行篡改和扭曲,这是极不可取的。
界面文化:你怎么解决外来词汇的中文化问题,是不是有时不得已需要自己制造新词?
马爱农:关于在翻译过程中创作新词的问题,我们在“哈利·波特”系列丛书中经常碰到。这套作品中的魔法世界,是基于西方巫师文化、魔法传说,再加上作者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而建立的,其中的一些咒语、魔法生物等都是凭空幻想,在字典上无从查询,也没有其他译法可以参考,所以要求译者展开自己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幽默感,充分调动自己的汉语词汇积累,给每个名词找到合适的译名。比如书中林林总总的咒语:幻影移形,倒挂金钟,原形毕现……;比如那些魔法生物:护树罗锅、嗅嗅、炸尾螺、蒲绒绒……等等。翻译每一个新的咒语和魔法生物,对我们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正如严复所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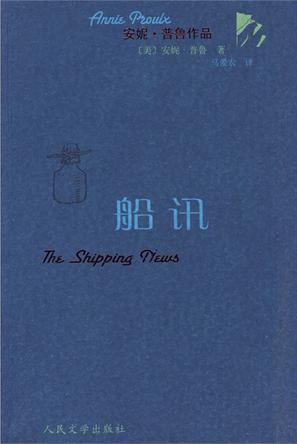
马爱农:《船讯》是美国作家安妮·普鲁的小说,获199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1994年普利策小说奖。故事讲述一个失败的中年男子重获新生的故事。全书以粗砺平淡的风格,压抑的深情如同潜流暗涌,仿佛是对那些被这世界唾弃却不自弃的边缘人、失意者内心褶皱和创伤的一次抚平与修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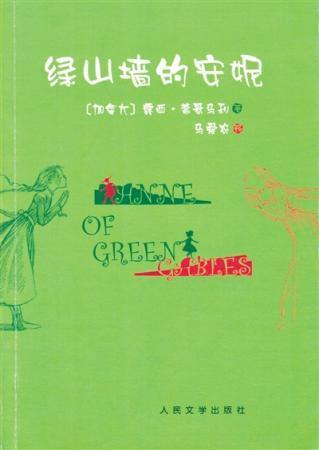
马爱农:加拿大作家露西·蒙哥马利(1874—1942)的代表作,讲述了一个感伤而充满诗意的故事。绿山墙农舍的卡思伯特兄妹本想领养一个男孩,不料阴错阳差,从孤儿院领回了女孩安妮。安妮长了一头红发,脸上有许多雀斑,一开始差点被退回去。但她纯洁正直、感情充沛,虽然身处逆境,却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幻想,终于在绿山墙找到了温暖的家。

马爱农:《走在蓝色的田野上》是爱尔兰当代女作家克莱尔·吉根(Claire Keegan)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作品描写了爱尔兰现代社会中绝望与欲望,精悍之中透着极其克制的冷调,情节起伏出人意料,让人惊叹在短篇格局中竟有如此跌宕的内容。译本曾于2014年获爱尔兰总领馆首届爱尔兰文学翻译奖。
马爱农:生于江苏南京,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现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要翻译作品有《船讯》、《到灯塔去》、《走在蓝色的田野上》、《爱伦·坡短篇小说选》等世界文学名著,和《绿山墙的安妮》、《绿野仙踪》、《彼得潘》、《古堡里的月亮公主》等儿童文学作品,她还参与翻译了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哈利·波特”系列作品。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